
7月15日至19日,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在山西省开展“文物保护法实施与文博事业发展监督性调研”。调研组先后深入山西省太原、长治、晋城市的文博单位详细了解文物保护法实施与文博事业发展情况,与基层干部群众交流,并举行座谈会,听取山西省相关职能部门工作汇报,委员们就有关问题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期间,调研组全体成员还在武乡县八路军总部砖壁旧址开展主题教育党课活动,思想政治受到洗礼和锻炼,进一步增强了永葆初心、践行使命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全国政协委员、GDI理事长连玉明全程参与此次调研活动,并将调研感悟记录形成《太行之旅——山西文物、文化、文明考察调研札记》,特此刊载,以饕读者。
2019年7月15日 晴 太原
这次参加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组织的“文物保护法实施与文博事业发展监督性调研”,是去年“历史文化名城名镇保护调研”的继续和延伸。

太原是山西段调研的第一站。下午14时30分,调研组16位成员在中共十九届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常委、社会和法制委员会主任沈德咏组长的带领下,赴山西省博物院实地调研考察,一个半小时后召开座谈会,听取山西省政府相关部门工作汇报。
远古圣火与“最初中国”
山西是文物资源大省,素有“表里山河”之称,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4500万年前的垣曲“曙猿”,可能是世界上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灵长类动物的共同祖先。山西已发现旧石器时代早、中、晚三期文化遗存300余处。位于山西南部黄河转弯处的西侯度遗址,是中国已知最古老的旧石器时代人类文化遗存之一,距今约180万年,属早期直立人阶段。
20世纪50年代,在西侯度西南更靠近黄河转弯处,沿东岸长达13.5公里范围内,以匼河为中心,发现有20个旧石器文化地点,属于80万年前晚期直立人阶段的典型文化遗址群。匼河文化与后来的丁村文化有着密切关系,共同构成华北旧石器文化传统的本体,并接近人类和文明的起源。
“山西地处黄河中游,华夏腹地,山川秀美,气候宜人,是中国远古人类和文明的摇篮。母亲河九曲如龙,奔流向东,在其最大最急的转弯处,有一个叫‘西侯度’的小山村。180万年前,这里的人们制造出中国最早的石器工具,燃起了中国第一堆文明之火,沧海桑田,生生不息。远古人类艰难的足迹踏遍了太行和吕梁之间,不灭的篝火闪烁在汾水与桑干两岸。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创造的灿烂文化,遍布山西南北。涓涓细流,百川归海,星散古国,辐辕升华。塔尔山下,尘封4500年后重见天日的城市、宫殿、文字、铜器、礼器、观象台和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龙,昭示着我们的祖先跨进文明之门。最早的‘中国’人从这里出发,走向未来。”
这段镌刻在山西博物院的开宗文字,无不让人对山西的文物、文化和文明肃然起敬。
陶寺遗址与良渚文化
陶寺遗址距今4300~3900年,空间和时间都与传说中的“尧都平阳”非常吻合。更令人耳目一新的是,考古发掘所展现出的最早的测日影天文观测系统、最早的文字、最古老的乐器、最早的龙图腾、最早的建筑板瓦以及黄河中游史前最大的墓葬,标志着黄河流域早期国家形态的诞生。
值得一提的是陶寺观象台。在陶寺文化晚期地层中, 揭露出一座由11个不同截面的夯土柱基排列成圆弧形态的组合建筑基址,布局与形制特殊,学者推测这是一座具备授时功能的古代观象台。根据模拟复原观测,在圆弧半径10.5米的圆心位置上,可以看到太阳从塔尔山特定的峰峦间升起,阳光直射到特定的柱间缝隙,从而确定一年中某些特定的时日(如春分、秋分、冬至、夏至)。如果这样的结论最终被确认,那么就应当是《尚书·尧典》中天文学知识体系的真实历史背景,从而可能形成中国二十四节气的重要源头。从另一个侧面,也可证明陶唐古国已进入稳定的农耕生活。
在西方史学界,认为文明的形成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城市;二是文字;三是器皿(主要指青铜器)。在陶寺遗址的一件陶扁壶残片上,发现有红颜料书写的“文”字,字的结体与殷墟甲骨所见几无差异。字有笔锋,似为毛笔类书写。这一重要发现,加之城市、宫殿、王墓、青铜和“礼器”,足足把中华文明向前推移至4300年。
良渚文化分布的中心地区在钱塘江流域和太湖流域,距今5300-4300年左右。良渚遗址考古发掘的最大成果是数量之多、品种之丰富、雕琢之精美的玉器,达到史前玉器的高峰。虽然玉器和陶器上出现了不少刻画符号,但并没有发现真正意义上的文字。尽管如此,良渚古城遗址仍是人类早期城市文明的范例,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2019年7月6日,中国良渚古城遗址获准列入世界遗产目录。申遗的成功,标志着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得到国际社会认可。
“五个全国第一”
与“三个不相适应”
山西历史悠久,人文灿烂。现存不可移动文物53875处。其中,古遗址13477处、古墓葬4298处、古建筑28027处、石窟寺及石刻1112处、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6715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52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487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2466处。文物系统备案博物馆150座,普查登记馆藏文物320余万件,有国家一级博物馆3座,二级博物馆13座,三级博物馆11座。从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看,现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6座,省级历史文化名城6座、历史文化街区25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15个、历史文化名城96个,中国传统村落545个,各级政府公布历史建筑1733处。
地下文物看陕西,地上文物看山西。山西文物在全国的地位可以从“五个全国第一”窥见一斑,即国保单位数量全国第一;现存旧石器时代遗址数量全国第一;现存元代及元代以前古建筑数量全国第一,特别是全国仅存的四座唐代建筑、全国75%以上的元代以前木构建筑均在山西;现存唐代以来彩塑和壁画数量全国第一;现存古戏台数量全国第一。
但从文物传承、保护和利用的角度看,“五个全国第一”的背后却反映出“三个不相适应”:
一是作为数量最多、资源最丰富的文物大省与山西转型发展、文化强省的战略地位不相适应。山西的转型发展必须走文化强省之路。现在的问题是,不能割裂地就文物谈文物,而是要把文物、文博、文化、文明统筹起来并上升为转型发展战略。文化一旦上升为战略,必然成为引领全局、覆盖全面、贯彻始终的强大推动力。如果资源不能变成资产和资本,那么就一定变成包袱和成本。比较陶寺遗址与良渚文化,应该说,良渚文化并没有陶寺遗址的优势,但良渚文化在考古发掘、文物保护、活化利用,特别是申遗方面却走在了陶寺遗址各项工作的前面。
二是山西文物特别是国保、省保单位数量、规模以及价值与国家、省对文保的投入不相适应。我们关注到,山西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52处,约占全国总数4295处的10.5%,位居全国第一。但从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分配看,是不是国家给予山西的文保资金也占到全国总资金的10%,是否也位列全国第一?从省级文物保护专项资金看,2011年到2019年年均增长22.5%,2019年达到1.67亿元。如果把1.67亿元放在2018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292.6亿中计算,所占比例只有0.07%,还不足千分之一。如果从文物真正保护的意义上看,1.6亿元还不足以修复一座早期遭到严重破坏的古建筑。
三是文物安全形势与文物保护力度不相适应。长期以来,一些地方盗掘古墓葬案件多发,特别是襄汾陶寺北墓地系列盗掘古墓葬案,对文物造成的严重威胁甚至是毁灭性破坏不言而喻。从山西省公安厅提供的材料看,2018年4月至2019年6月底,全省公安机关共破获文物犯罪案件963起,抓获犯罪嫌疑人数和追缴文物数均超过前十年总和。经权威机构和专家鉴定,这些珍贵文物上至商周、下至明清,几乎涵盖了中华文明进程的每一个时代,或成为诠释中华文明起源的有力实证。特别是在向文物部门移交的25415件文物中,一级文物130件,二级文物265件,三级文物928件。以此可见,盗掘古墓葬仍十分猖獗,而文物保护力量却很薄弱,打击文物犯罪特别是盗掘墓葬行为并非一时之力,亟需形成合力,并持续加大力度。
2019年7月16日 晴 长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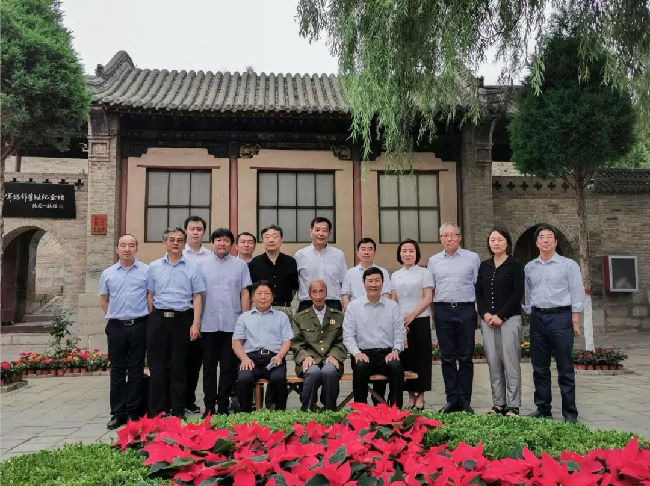
从太原到长治,一天的奔波。八路军太行纪念馆的感动、王家峪旧址的激励、砖壁旧址的洗礼,劳顿与疲倦荡然无存。夜虽深,睡意无,遂写下这段文字。
八路军太行纪念馆位于山西武乡,这是一座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丰碑。从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迹,到中国工农红军主力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东渡黄河,开赴华北抗日前线。从宝塔山麓到黄河之滨,从长城内外到陇海沿线,英勇无畏的八路军将士,前赴后继,浴血奋战,在中国抗战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惊天动地、惊心动魄的人民战争活剧,迫使日军陷入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谱写了光辉的篇章。纪念馆的数据显示,八路军从1937年的8万人发展壮大到1945年的102.8万人。另一组数据显示,从1937年9月到1945年10月,八路军共作战99847次,毙伤日军40.16万人,八路军伤亡34.71万人。依此推算,八路军每一个战役平均毙伤日军4人,八路军伤亡3.5人。可见其战事之惨烈。1939年11月,朱德总司令在王家峪八路军总部赋诗《寄语蜀中父老》:“伫马太行侧,十月雪飞白。战士仍衣单,夜夜杀倭贼。”正是这种太行精神,成为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的力量源泉。
从武乡县城去往王家峪旧址途中,我们参观了“地雷大王王来法纪念馆”。这是一位普普通通的抗战英雄。长乐战斗后,八路军民运工作队驻于李峪村开展群众运动。1941年5月,李峪村武委会主任王来法参加地雷训练班,学习爆破技术和装雷、埋雷技能,迅速组织村民以雷制敌,并编出《地雷战民谣》:“鬼子来了咱不怕,给他一颗铁西瓜。铁西瓜,铁西瓜,鬼子一踏就开花”。
在武乡,仅有14万人口的小县,就有9万多人参加了各种抗日团体,14600人参加了八路军,5380人外调抗日干部,抗日支前勤工387万工日,为部队筹粮240万石,妇女做军鞋494500双,织米袋、挎包、慰问袋107500件,提供蔬菜、油等副食507500斤。其中有2.1万余名干部群众为国捐躯,留下“出兵出粮出干部,五千干部一万兵”的佳话。
2009年5月25日,习近平同志调研武乡时提出:“要始终保持对党对人民对事业的忠诚,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始终保持知难而进、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正如《太行民谣》唱的那样:“金太行,银太行,铜墙铁壁钢太行。太行人民乐洋洋,鬼子见了心发慌。为什么太行这样强?共产党领导打东洋,拨开云雾见晴天,天晴有了红太阳。”
在王家峪旧址纪念馆,我们瞻仰了彭德怀于民国三十一年双十节(即1942年10月10日)为左权将军撰书的碑志:
左权同志湖南醴陵人,幼聪敏,性沉静。稍长,读书既务实用。向往真理尤切。一九二四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献身革命,生死以之。始学于黄埔军校,继攻于苏联陆大。业成归国,戮力军事,埋头苦干,虚怀若谷,虽临百险乐然不疲,以孱弱领军长征,倍见积极果决之精神。中国红军之艰难缔造,实与有力焉追乎。七七事变后,倭寇侵凌,我军奋起抗敌作战,几过中原,同志膺我军副参谋长之重任,五年一日建树实多,不幸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五日清漳河战役,率偏师于十倍之倭贼斗,遽以英勇殉国,闻得年仅三十有六。壮志未成,遗恨太行,露冷风凄,恸失全民优秀之指挥。隆冢丰碑,永昭坚忍不拔之毅魄。德怀相与也,深相知更切,用书梗概,勒石以铭是为志。
1949年,解放军南下解放全中国,朱德总司令命令所有入湘部队,都要绕道醴陵去看望左权将军的母亲。直到此时,老人仍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已经殉国。当得知左权牺牲后,他的老母请人代笔,为儿子写下这样的祭文:“吾儿抗日成仁,死得其所,不愧有志男儿。现已得着民主解放成功,牺牲一身,有何足惜,吾儿有知,地下瞑目矣!”
在砖壁旧址院落的彭总榆下,我们聆听了90岁高龄、被朱德总司令任命为儿童团团长的肖江河老人讲述的抗战经历与抗战故事。1939年至1942年间,八路军总部机关曾先后四次进驻砖壁村,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左权等老一辈革命家曾在此长期生活和战斗。八路军总部在砖壁驻扎期间,指挥了华北抗日根据地许多重大战役,特别是在此部署和指挥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1940年8月20日至1941年1月24日,历时5个月,八路军参战兵力105个团,日军参战兵力20余万人、伪军约15万人、飞机150余架,作战共计1824次,死伤日军20645人、伪军5155人,缴获各种装备、武器、弹药不计其数,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在中华民族不畏强敌、争取独立解放的历史上书写了光辉的一页。
伫立在这些革命文物面前,思绪万千。不管走多远,都不要忘记来时的路。革命文物凝结着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历史,展现着近代以来中国人民英勇奋斗的壮丽篇章,是革命文化的物质载体,是激发爱国热情、振奋民族精神、坚定“四个自信”的深厚滋养,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力量源泉。不论是文物管理者还是文化工作者,特别是党政决策者,应当充分认识加强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的重大意义,更应当把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放在文物保护工作更加突出的地位。
2019年7月18日 晴 晋城
(一)
这几天的收获是丰盛的。一路走,一路看,一路想。如果把这些收获概括起来,可以分三个层面:
这是一次文物之旅。山西文物遍布,上下五千年,纵横八百里。每一处都有讲不完的故事,每一个故事都令人震撼。仅以晋城市泽州县为例,境内现存文物1611处,全省第一。其中,国保19处,省保9处,市保94处,县保35处,尚未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还有1454处。各级文保单位星罗棋布、遍及城乡,上起汉唐,绵延宋、辽、金、元,下迄晚清。单就“大禹治水”丹河龙头、“女娲补天”浮山娲皇宫、“三藏取经”摩崖造像、“三姑发水淹怀庆”三姑泉等足以令人神往。
这是一次文化之旅。以太行古堡为例,在晋城30平方公里范围内,遗存的古堡多达117处,以湘峪古堡、皇城相府、郭峪古堡、砥洎城为代表,已经形成沁河、丹河两岸的古堡古寨古村群。这是太行山南段独具特色的文化密集区。深藏于太行深处的古镇古村,独守静谧,依然坚守着纯朴的世外桃源气质。亲身体验的高平良户、苏庄两个历史文化名村,如同走进藏风聚气的五福圣地、怡情养性的天然氧吧。各具特色的建筑风貌像一本本鲜活的教科书,每一个人都能体味到“凝固的音乐、石头的史书”之美。街头巷尾的上党戏曲,继承了唐代梨园的风范,演绎着千年的历史传奇。太行之行,不愧为山水寻秘之行、古韵古村之行、古建寻福之行、乡愁寻美之行、民俗文化之行。
这是一次文明之旅。这次未能考察羊头山,而改道炎帝陵。如今的炎帝陵已在原址上进行了改扩建,建设用地160余亩,规模宏大,气势宏伟。整个建筑群依中轴线由南向北拾阶而上,依次布置有山门、功德殿、始祖殿、炎帝大殿四进三重院落。中轴线两侧分置钟鼓亭、聚贤堂、关圣殿、颂德堂、医药堂、根源堂、溯源堂、百草殿、五谷殿、农耕堂、碑亭、碑廊等,古建群均为木结构,采用晋东南传统祭祀建筑手法和宋式建筑风格。炎帝大殿庄严肃穆,大殿中央供奉着黑脸神农炎帝(传说因“种五谷、尝百草”所致)。每年农历四月初八炎帝诞辰之日,在此举办海峡两岸神农炎帝故里民间拜祖典礼。
炎帝是中华农耕文明的开创者,所种五谷为“黍、稷、菽、麦、稻”,其实就是北方的杂粮。五谷之首为“黍”就是现在的谷子,或称“小米”。上党“小米”闻名天下,“沁州黄”“泽州香”千百年来都是御用贡品。高平鼓书《谷子好》唱的是著名山药蛋派作家赵树理的歌词:
谷子好,谷子好,吃得香,费得少;
你要能吃一斤面,半斤小米管你饱。
爱稀你就熬稀粥,爱干就把捞饭捞;
磨成糊糊摊煎饼,满身窟窿赛面包。
就在太行之行即将结束之际,晋城市委书记张志川又讲起一段“昆仑丘”的神话传奇。他说中国科学院科学家华仁葵团队历时十七年考证,提出“昆仑丘、天台山是中华文明发祥地,也是大道文化原创地”的新论断。当然,这只是“中华文明多源说”中的其中一种学说,但它的考证与研究,必将还原中华初始文明史以本原本貌。
(二)
这几天的心情是复杂的。这种复杂是基于山西文物资源这么多“中国第一”“中国唯一”“中国之最”背后的巨大反差,也是作为山西人对家乡的情怀与情感交织在一起的些许无奈。这种复杂中既有震撼,也有遗憾;既有感叹,也有感慨;既看到家乡人的自豪,也看到自豪背后的一点自负。山西文物、文化、文明所担负的历史厚重是毋庸置疑的。但现实的观照总给人一些不够、不足、不当,这些“不”难以抚慰和填补内心的不安与空白。如果把这种复杂的心情变为一种反思与反省,则得出以下一些基本结论:
第一,研究不够。山西人对文化的挚爱刻骨铭心。无论是沾满“黑金”的双手,还是腰缠万贯的“暴发户”,都能轻松自如高举文化这张“王牌”,在人前滔滔不绝讲起一个又一个文化故事。当人人高呼山西文物全国第一的口号时,对文化价值的挖掘与研究则片言只语,这与发达地区形成鲜明反差。陶寺遗址无论从中华文明史还是西方文明史的角度都可考证为中华文明之源头,但申遗成功的却是浙江的良渚文化。一路走过,听到的传说故事多之又多,但能收集的文献则少之又少。文存的价值在于传承。传承不仅仅是口口相传,而是基于挖掘与研究的文献记载与文字记忆。山西不缺文物,缺的是对文物的挖掘;山西不缺文化,缺的是对文化的深耕;山西不缺文明,缺的是对文明的敬畏。“一煤独大”富了山西,也毁了山西。对文化表面的认知本身就是一种肤浅。
第二,保护不够。保护是针对破坏而言的。根据我多年的研究,把文物或遗存破坏分为十一类,即掠夺式破坏、灾难式破坏、运动式破坏、人为式破坏、自然式破坏、开发式破坏、修复式破坏、观光式破坏、流失式破坏、发掘式破坏和放任式破坏。保护是为了不被破坏。之所以把破坏分类分析,旨在期待保护者精准施策,提出针对性保护方案。从上述破坏类别看山西文物保护,或多或少,或轻或重,皆而有之。对山西历史文化遗产来说,最紧要的有两件事:一是对独一无二并处于高濒危的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和石刻、壁画必须实施抢救性保护。当然,提出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悖论,核心是钱从哪儿来。我个人的观点,对山西而言,钱是问题,也不是问题。关键是我们怎么想。想通了,钱也就来了;想不通,只能解释为有心无力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如何抢救。莫高窟的数字化保护为我们提供了成功先例;二是对遍布南北的古村落的保护,这是山西无与伦比的独特文化资源。我们看到了修缮、开发和利用,看到了政府积极推动的守护认养制度,但我们忧虑的是在修缮、开发、利用中不知不觉的被破坏。从文物保护角度看,政府主导是好事,社会参与也是好事。如果从某种意义上讲,既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也可以集中力量办坏事。我们推动文旅融合、活化利用,我们期待文化成为旅游的灵魂,而不是把文化变成旅游的牺牲品。
第三,宣传不够。宣传不等于轰轰烈烈、声势浩大,形式只是一个方面,关键看效果。宣传也不能只靠自个儿喊,即使嗓门再大,能听到的也就那么几个人。山西是文物大省、文化大省,文物大省要有文物大省的样子,文化大省要有文化大省的形象。塑造这个“样子”和“形象”就必须有新思维。在这方面应着力把握以下三点:一是跳出山西看山西,跳出文物看文物。文化是人类精神的张扬,并非必须实用。用实用主义思维对待文化,可能得不到任何效用,反而把文化也糟蹋了;二是整体策划、整体包装、整体推介,不能再碎片化、割据化,各吹各个号,各唱各个调;三是以历史语境、未来语境和全球语境,讲好山西故事,传承山西文化。
(三)
这几天的思绪是凝固的。为打破这种凝固,我从京东书城网购了五本书,即《感喟秋雨》《中华祖脉》《家国往事》《祖先,祖先》《山西笔记》,并一路狂读,以期作为我调研的指引。
这五本书的作者叫李琳之,是我大学的师弟,更是良师益友。这些年,他弃商从文,专注山西历史文化的研修与笔耕,成为中华文明源头的坚定探索者。他的书被誉为“重新观照华夏文明源头的坐标”。
谈山西文物、文化、文明之演变,必谈此人,也必谈此书。因为此人此书之影响已跳出山西式思维,并正融入中华文明“多源一体”的伟大洪流之中。至少以下三点可以唤醒另一层面上对山西文化和华夏文明的家国记忆:
第一点,在探寻中华文明源头上,李琳之付出艰辛努力并初步形成独到的论断。他以迪拜式思维颠覆了人们对中国上古史的传统认知,进而提出“山西是中华早期文明的孵化场,是中国历史上众多王朝的孵化场,是中华北方民族融合的孵化场 ”。这些论断“直接触摸到了中华文明原点的脉搏所在”。
第二点,李琳之的作品对山西文物、文化、文明作出系统性挖掘,不偏不倚,从根本上扭转了过分拔高晋中、过度倚重晋南的文化现象。李琳之对山西历史文化的追索,是亲历与考证,是跋涉与体认,是史观与史识的重构,是反思与反省的传承。作为文化学者,他带给我们有温度而又理性的思考。作为散文作家,他却能对一山一水、一草一木赋予历史厚重与文化内涵,让人在涓涓细流中激荡心灵的震撼。
第三点,李琳之的研究方法和写作风格耳目一新。这种调研式、考证式散文值得推崇,并值得政协调研借鉴。从某种意义上说,李琳之的文章与其说是写出来的,不如说是“跑”出来的。每一篇文章、每一个考证、每一种探寻的背后都浸透着他脚下泥土的芳香。在他身上,用“千山万水、千家万户、千辛万苦、千难万险、千方百计、千言万语”的“六千”精神形容已不为过。这种“文人功业,赤子情怀”,不正是山西所期待的吗?!
2019年7月19日 晴 北京
这次山西之行,虽短短五天,但震撼很大,感触极深。透过山西文物保护与文博发展的监督性调研,折射出文物保护的诸多现实问题。现将座谈会上未尽之言简略如下,以期对文物保护法修订有所启迪。

第一,重新认识文物保护的时代价值。从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批示精神中更加深刻领会和把握文物保护的精髓与本质。比如全面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工作方针,切实加大文物保护力度,推进文物合理适度利用;不能搞“拆真古迹、建假古董”那样的蠢事;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修旧如旧,保留原貌,防止建设性破坏;要正确处理文物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关系,做到保护第一、开发第二,坚决禁止破坏性开发;任何个人和单位都不能为了谋取眼前或局部利益而破坏社会和后代的利益。这些话,核心只有两个字,就是保护。
第二,以文物保护法修订为重大契机,构建和完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体系和政策体系。必须指出的是,现行法律法规严重滞后于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实践,严重制约了历史文化遗产的原真性与完整性保护。建议尽快修订《文物保护法》《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尽快把《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法》提上国家立法议事日程,加紧研究制定《传统村落保护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法》,逐步形成完整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法律体系。在此基础上,加快构建和完善与之相适应的政策体系,以期法律法规的落地落实。对山西文物保护实施与文博事业发展的监督性调研再一次充分说明,历史文化遗产最有效的保护首先是立法保护。核心的问题是理顺文物保护的体制机制,避免政出多门,各自为政。
第三,把革命文物保护放在文物保护和文博事业发展更加突出的地位。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迫切需要加强革命文物资源整合、统筹规划和全面保护、整体保护,迫切需要统筹推进抢救性保护与预防性保护、文物本体与周边环境保护,确保革命文物的历史真实性、风貌完整性和文化延续性。建议建立健全革命文物集中连片保护利用机制,对重大事物遗址、重要会议遗址、重要机构旧址、重要人物旧居要做到有址可寻、有物可看、有史可讲、有事可说。文物保护法修订中应对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做出专门规定,并加紧研究制定《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法》。
第四,正确认识文物保护与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特别是传统村落保护的关系。观察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重要分水岭是以党的十九大为标志的机构改革。为什么要重组文化和旅游部,最根本的就是要推动文化与旅游的融合发展。而融合发展的核心是历史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活化利用既是文旅融合的方向,也是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重心。从文物保护的角度看,关键问题是如何合理适度利用。从传统村落保护的角度看,关键是如何更好地推动活化利用。传统村落不一定是文物,但作为历史遗存需要保护和传承。活化利用并不等于大拆大建、拆旧建新、整体搬迁、商业开发。而是充分利用老建筑、老街坊、老遗址、老物件、老居民、老故事,把传统村落找出来、保下来、串起来,让游客走进来、住下来、讲出来,让历史文化遗产真正活起来、亮起来、火起来。
第五,高度重视现代科技特别是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在文物保护与文博事业发展中的运用。对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壁画等高度濒危的不可移动物,应当运用数字化记录、数字化修复、数字化传播方式进行抢救性保护。核心是亟待解决文物保护特别是数字化保护专业人才队伍和资金投入问题。必须指出的是,文物是公共产品,文物保护首先是政府责任。对国保、省保文物应加大公共财政投入力度,国保投入应按省保文物数量比例确定资金分配比例。对偏远地区或区域、缺乏保护条件、没有特定遗址价值和展示功能的不可移动文物,可适当整体或部分移至博物馆,这更有利于文物的长期保护、传承和传播。
有人提出,文物保护法的修订可否把文物保护法修改为文物保护利用法;也有人提出,传统村落保护的核心问题是古建筑的产权问题,可否研究制定更有利于资本进入的产权制度;还有人提出,文物保护、传统村落保护、革命文物保护可否在主管部门上采取集中统一管理而不是各自为政的情况等等,这些问题既是痛点,也是难点,更是修法的焦点。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GDI理事长连玉明)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Zd7nVTPD5DoPpLkF8BlTpA

